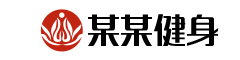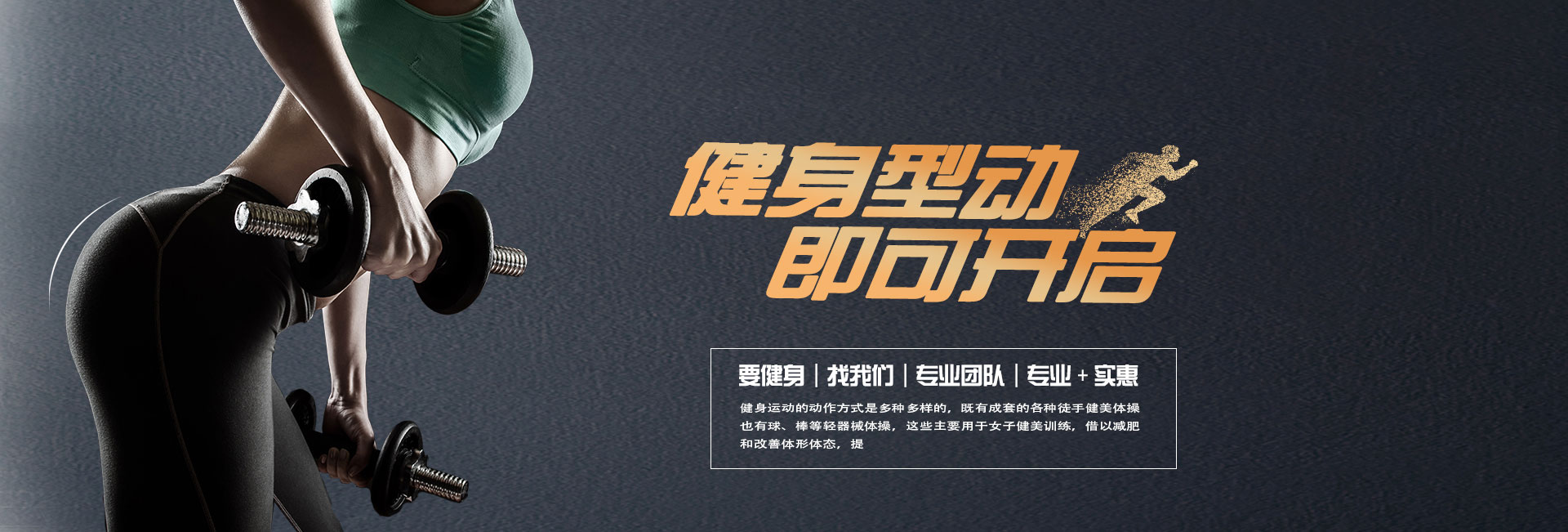在信息爆炸的21世纪,知识从未如此触手可及,却也从未如此支离破碎。当专业教育将学生训练成“精密零件”时,通识教育(Liberal Education)正试图回答一个古老而紧迫的问题:教育究竟是为了培养“有用的工具”,还是造就“完整的人”?
哈佛大学1945年发布的《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》报告中,将通识教育定义为“培养人作为负责任的人、公民和艺术家的教育”。然而在就业率至上的今天,这种理念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中国某985高校的调查显示,67%的学生认为通识课程是“凑学分的选择”,38%的教师承认“为迎合学生降低课程难度”。更吊诡的是,在MOOC平台拥有百万订阅的《西方哲学史》课程,其本校选修人数却不足30人。这种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的现象,暴露出通识教育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。
麻省理工学院要求所有工科生必修人文课程,其课程说明中写道:“我们需要能思考伦理的物理学家。”这种设计直指专业教育的盲区——当人工智能专家不懂哲学,基因编辑科学家缺乏伦理训练,技术进步就可能沦为危险的狂欢。
斯坦福大学的“批判性思维与写作”课程中,学生需要比较《宣言》与《国富论》的底层逻辑。这种训练不是要灌输结论,而是培养“质疑一切既定答案”的思维能力。正如哲学家罗素所言:“大多数人宁愿死去,也不愿思考。”
台湾大学的白先勇教授开设《昆曲赏析》课时,特意安排在工学院教学楼。他说:“当理工生能分辨《牡丹亭》与《长生殿》的区别,文化传承才算真正成功。”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,正是通识教育最动人的力量。
芝加哥大学的“经典阅读计划”要求所有新生共同研读《理想国》。校长罗伯特·齐默认为:“当年轻人与苏格拉底对话时,他们不仅在读书,更在练习如何做人。”
哥伦比亚大学的“核心课程”坚持百年不变,所有学生必须修读《荷马史诗》到《存在与时间》的经典文本。其教务长曾幽默地说:“我们的课程表比校园里的橡树还要古老。”
东京大学将大一新生全部编入“教养学部”,实施不分专业的通识教育。这种“延迟专业化”的设计,使得日本诺贝尔奖得主中,超过60%本科阶段接受过系统通识教育。
复旦大学“通识核心课程”采用“大班授课+小班研讨”模式,要求每位教授必须亲自带领讨论。其《医学与人文》课程甚至邀请临终患者走进课堂,让医学生在解剖学之外,理解生命的重量。
当GPT-4能瞬间生成论文,当专业知识的半衰期缩短至2-3年,通识教育的价值反而愈发凸显。它要解决的,恰恰是机器无法替代的人类命题:
北大教授钱理群曾警告:“我们正在培养‘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’。”而通识教育或许正是解药——它不是要教人“知道什么”,而是要让人明白“为什么值得知道”。
1936年,爱因斯坦在《论教育》中写道:“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,专业教育可以让人成为有用的机器,但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。”
在某个复旦大学的深夜教室里,哲学系的最后一节《死亡哲学》课即将结束。教授放下粉笔问道:“现在谁能告诉我,苏格拉底饮下毒酒时,真正教会我们的是什么?”沉默中,一位物理系的学生举手回答:“是让我们学会检验,自己此刻活着的生活,是否经得起死亡的审视。”
这一刻,通识教育完成了它最本质的使命——不是传授知识,而是点燃思考的火种;不是培养某个职业的人,而是唤醒人之为人的自觉。当所有具体知识都被遗忘后,这种照亮生命的力量,才是教育留给一个人真正的遗产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